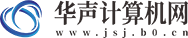直到现在,每次吃带骨头的肉,袁靖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这是什么动物的什么骨头”。他笑称,这是动物考古学家的“通病”。
四川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鸡
 【资料图】
【资料图】
河南殷墟54号墓的牛尊
清代玉嵌宝石卧兔
东吴时期青瓷羊形灯
94年前,当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时,整个世界都为之瞩目,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洞穴堆积里还有小小的老鼠。
在这个距今数十万年前的遗址中,除了古人类的骨骼,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些散碎的鼠类骨骼。但这些小小的动物当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即使它是这个地球上更古老的动物——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历史仅不到300万年,而鼠的存在至少长达5500万年。小小的鼠,或许才因此被称为“老”鼠。
动物考古学家、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把自己30余年的考古生涯贡献给了这些不被优先考虑的动物们。不管是老鼠1厘米长的骨骼,还是黄牛的前腿后腿,他都辨得出来。
1995年,袁靖在河南班村遗址做动物考古,从七八百块动物骨骼里,拼出了7头年龄大小不一的猪。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看了这7副骨架,兴奋地给袁靖打电话:“我们拼陶片拼了几十年,但是拼对动物骨骼,是从你这儿开始的!”
从12种生肖动物重新认识华夏文明的细节
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探索,动物考古研究的是古代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古人怎么利用动物、这个过程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什么作用、人类的活动又对动物本身造成了什么影响。”袁靖以谦卑的姿态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离开人类,动物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寸步难行。”
最近,他在出版的新书《动物寻古》中,妙趣横生地讲述了12种生肖动物背后的考古故事,带人们重新认识华夏文明中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比如,猪被驯化之前,曾是勇敢和有力的象征,西汉之前还有人以 “彘”为名;“狗拿耗子”也并非“多管闲事”,而可能是比“猫抓老鼠”更历史悠久的事。
人类与动物最早的亲密连接始于狗,狗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家养动物。袁靖认为,养狗的行为丰富了古人对友情的认知,“有了狗,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路途中就不再孤单了”。
这是从骨头中找到的答案。我国华北地区就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有驯化痕迹的狗骨。在距今8500余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十几具被埋在墓葬区附近的狗骨,这显示出人类与狗的特殊关系。最典型的是商代殷墟的腰坑殉狗:考古研究人员在发掘墓葬时先发现人骨,人骨清理掉以后,发现腰部位置还有一个小坑,放着一只狗,有的狗脖子附近还有铜铃。与此同时,骨骼检测的结果也表明,狗的食物结构的变化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古人食物结构的变化轨迹完全同步,在距今约7000年之后,狗的食物开始以粟作农产品为主,说明狗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学会养狗之后,古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猪。他们于大约9000年前开始养猪。相比黄牛、绵羊、山羊、马和鸡是被驯化成家养动物后才引入中国,猪是在中国本土驯化的。
袁靖将猪的驯化、饲养和选育技术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口增长、社会复杂化发展、文明的起源和进步都与此有关。他的研究证实:尤其以黄河流域史前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最为明显,猪越来越多,鹿越来越少,也就是家养动物越来越多,狩猎动物越来越少。“社会发展了,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活动空间不断扩大,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就缩小,也不容易获取了,古人就开发出通过饲养家畜的方式保证稳定的肉食资源供应。”袁靖解释。
考古学家常常发现破碎的猪骨,这是古人敲骨吸髓的痕迹。而对另外两种对人类历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动物——牛和马——而言,骨骼上保留着十分重要的信息。动物考古学家曾在它们的骨骼中发现骨质增生的现象:“过度役使家养动物,劳动强度超出其生理负荷,往往会在这些动物的骨骼上留下骨质增生等病变的痕迹。”
牛和马,分别肩负着人类的农业和军事重任。牛耕是古代生产力的第一次重大飞跃,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牛在农业社会里的超高地位,唐玄宗还专门下诏书,禁止随便杀牛。马则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动物寻古》中提到:“被人当作坐骑的马,其脊椎骨上往往会留下骨质增生、发育不对称、脊椎融合、水平裂缝等多种病变迹象……位置与人骑乘的位置正好重合。”
袁靖(2018年摄于北京王府井动物考古实验室)
每次吃带骨头的肉,习惯性地看一下“这是什么动物的什么骨头”
从一块小小的骨头中,看到动物们活着的瞬间,包括它们从哪儿来、吃了什么、死于何时,这是“识骨寻踪”的魅力。在采集动物遗存之后,动物考古学家会进行种属部位的鉴定、测量和统计,再进行碳14测定、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检测。
在这之前,动物考古首先要掌握动物分类学和解剖学的知识,并且讲究“将今论古”,即通过现生的动物骨骼来学习、比对出土的古代动物骨骼。国外一些学校动物考古学课程的期末作业,就是交上去一副鱼的骨骼。袁靖也动手自己做,蒸一只鸡,把肉都剔掉,得到一整副骨骼。后来,他的一位学生家里制皮革,还帮他做过整副牛、羊的骨骼。
除了完整的骨头,碎骨之所以破碎的种种痕迹也值得观察。为此,他会去看狗是怎么吃骨头的。“一下就把骨头关节部位咬碎了,但骨干它咬不动。”袁靖说。有些动物骨骼在出土时就是破碎的,在做鉴定时最好有一个对比的同类动物标本。上世纪30年代,殷墟考古发掘时,负责动物考古的地质学家刘东生就是去肉铺买骨头,拿回来做标本,比照研究。“我们现在建设动物考古实验室,建得好不好,标准之一就是看收藏的现生的动物骨骼标本多不多。”袁靖说。
直到现在,每次吃带骨头的肉,袁靖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这是什么动物的什么骨头”。他笑称,这是动物考古学家的“通病”。几年前,他的几位学生在外面吃饭,点了一份烤羊腿。吃着吃着,除了味道似乎不对之外,发现了肩胛骨,说明这是一条前腿。但仔细一看,肩胛骨的关节特征不对——猪的肩胛臼是椭圆形的,而羊的肩胛臼是圆形的。另外,连着肩胛骨的肱骨、桡骨等都是猪的,不是羊的。几位动物考古学者叫来了饭店老板,告诉他,这是一条猪前腿,不是羊腿。老板起初极力否认,直到他们用猪和羊的骨骼形态特征层层论证,说得老板“心服口服”,才退钱免单。
修正了动物的历史,人的故事也会随之印证或变动
拼骨头,袁靖不认为是难事。他之所以是俞伟超所说的“第一个拼动物骨架的人”,是因为在此之前,“采集不采集动物骨骼,用不用科学的方法采集动物骨骼,这些都是问题”。袁靖说:“前辈考古学者发掘的时候,普遍认为人工的遗物是重要的,陶片、石器是重要的。动物考古做的人少,对采集动物骨骼的重要性的认识很晚才树立起来。”
上世纪30年代,殷墟考古拉开了中国动物考古的序幕,这被袁靖称为“灿烂的开篇”。但其后20余年,由于战争等原因,中国的田野考古和动物考古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上世纪50年代,两位古生物学家对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研究报告,重新开启动物考古研究。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才开始专门配备做动物考古的研究人员。
1989年,袁靖到日本留学。导师加藤晋平教授和他第一次见面,给他设计了3条路:一是继续学习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但我教不了你,因为我不懂”;二是学习日本考古学,“但回去了怎么用”;三是学动物考古,“这在国际上是前沿,你可以回国去发挥作用”。袁靖当即表态,要选第三条路。
当时,中国考古的主流研究是“建谱系”。“比如北京地区1万年以前是怎样的——但不是说社会形态是怎么样的,而是陶器、石器、墓葬的形状是怎样,要把文化谱系构架起来。”这在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做了,因此,在日本听到动物考古的袁靖,立马兴奋起来。
求学4年,一直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袁靖都在脑子里琢磨:“回国以后该怎么做?在哪儿做?我要做出什么来?”没有现成的答案。1993年,袁靖学成归国,到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初试锋芒”。他从北京坐了4小时的车过去,考古队员将他带到一个半地穴式的房子前,揭开塑料布,一堆动物骨头露了出来。
这是他的职业生涯中至今难忘的瞬间,因为他立马认出了那些骨头是什么动物的什么部位。“一下子心里就有底了。因为我认识它,我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我要观察哪些迹象、测量哪些部位,这都是学过的,实践就行了。”他豁然开朗,“我有能力在中国的考古工地上开展研究了。”
在之后的考古研究中,袁靖修正了以往认为家鸡最早是起源于距今约8000年前的中国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误解,认定以前的骨骼鉴定有问题,中国有科学鉴定的家鸡最早发现在距今3300年前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他在法国提起这个问题时,有人说“你回去以后,有些人要不高兴的,你把一个‘中国最早’的观点推翻了。”他回应对方:“科学就是科学。”在袁靖看来,考古是“实打实的”,他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系统材料为自己的研究佐证。
修正了动物的历史,人的故事也会随之印证或变动。为周朝养马起家的秦人,其祖先来源问题曾在史学界引起争论,观点分为两派——“秦人东来说”和“秦人西来说”。动物考古学家后来发现,商人有以狗随葬的习俗,随着商朝灭亡,部分遗民被周人西迁到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一带,随葬狗的习俗也跟着在那一带出现。鉴于丧葬习俗是很难改变的,位于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一带的商人被推断为秦人的祖先,这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提到的秦人东来的记载是互相印证的。
用考古发现去还原史前的历史,还需要有一些想象力。这是更难的部分,现代思维与原始思维有很大差异,“数千年间因为没有文字流传而造成的思维传承的中断,绝非轻易可以重建的”。
袁靖提起法国学者写的《原始思维》中令他印象深刻的细节:原始部落的人靠自己的双手双脚计数,因此,他们没有20以上的数字概念,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家羊群的数量,他们用脑海里的图像计数。“这个知识不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而是口口相传。所以考古讲中程理论,就是借鉴大量民族学的调查去理解考古现象。”
这不容易做到,但值得为讲好华夏民族与动物同行的故事而去努力探索。